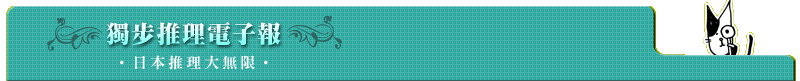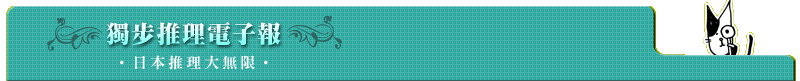1
很久以前,曾經有理髮店老闆告訴我,說他對頭髮沒啥興趣。「不就是用把剪刀剪下客人的頭髮嘛。從早上店門一開,到晚上關起店門為止,連個休息時間都沒有,就這麼一直卡嚓卡嚓地剪。當然囉,看到客人的頭逐漸變得清爽起來,感覺是還不錯啦,可是那並不是因為我喜歡頭髮才有這種感覺喔。」
五天後,那個老闆在街上被瘋子刺中腹部死了。當然說這段話的當下,他根本毫無警覺自己的死期將近,所以聲音中滿是快活且朝氣十足。
「如果真是這樣,那你幹嘛還當理髮師啊?」我隨即反問他。他臉上帶著苦笑這麼答道。
「因為那是工作。」
沒錯!跟我的想法相同,說得誇張點,就是跟我的處世哲學一致。
我對於人類的死亡根本毫無興致。無論是年輕總統在時速11英哩的遊行專用車上被狙擊,或是某地方的少年跟愛犬一塊兒凍死在法蘭德斯大畫家魯本斯的畫前,我一點都不在意。
說到這裡,我記得剛才那位理髮店老闆也曾提過「怕死」之類的話。當時我針對這句話問他:「你還記得出生前的事嗎?」「出生之前,你覺得害怕嗎?會痛嗎?」
「不會。」
「死亡不也就是那回事兒嘛,只是回復到你出生前的狀態罷了,根本沒啥恐怖,也不會感到痛楚。」
人死亡本身毫無意義,也不具任何價值。如果逆向思考,也就是說每個人的死亡其實是等同的價值。那也正是我之所以不對任何人、任何時間的死亡感到興趣的緣由所在。話雖如此,今天暫且撇開我有無興趣一事,我還是得專程趕往某地,確認某人死亡的相關事宜。
為什麼?因為那是我的職責所在。正如理髮店老闆所言。
我來到一棟大樓前方,此地離車站約一百公尺遠,是棟二十層樓高的電機廠商的辦公大樓。大樓牆壁閃閃發亮,對面天橋及大樓的緊急逃生梯皆清楚地倒映其上。我站在正門入口旁邊,無聊玩弄著摺好的傘。
頭頂上那一大片沉甸甸的烏雲,鼓脹得像是發達的肌肉,雨水筆直地灑落,縱使雨勢不強,卻讓人感覺這場霪雨將會頑強地繼續,永無停歇的一刻。
無論我何時開始工作,天候總是欠佳。我一度懷疑,或許只是因為「經手死亡」是我的工作,才會老是碰上壞天氣吧?但當我聽聞其他同事描述的經歷,卻似乎從未遇到類似像我這樣的狀況;這一切應該只是巧合吧。儘管明知當我說出「我在執勤時從未碰過晴天」之類的話時,別說是人類,就連我那些同事也對我投以無法置信的目光,但事實就是事實,我也無計可施。
我瞧了瞧時鐘,現在已經是十八點過三十分,根據我從情報部取得的行程表看來,也該是我現身的時刻。心裡剛這麼想著,正巧就看到她從自動門裡走出來,我便開始進行跟蹤她的任務。
她手裡撐著透明的塑膠傘,走路的樣子看上去相當陰沉,儘管她身材高挑、體態適中,不過值得讚美之處僅止於此。那女子不僅彎腰駝背、走路姿勢外八,再加上那副垂頭喪氣的樣子,整體給人的感覺比她實際的年齡二十二歲更顯得老成,此外她還將那頭烏黑的秀髮攏到腦後梳成包頭,這點也令人有種灰暗的印象。不知道該說是身心疲倦不堪、抑或是心中悲壯難抑,總覺得似乎有抹疲憊的影子籠罩著她整個頭部。不過看來像包裹在厚沉沉的鉛灰色中的她,恐怕不能只歸咎這場濡濕大地的雨吧!
我雖不認為她只要化了妝就會變得好看,但或許她本人也從未萌生過想要好好盛裝打扮的意念。甚至她此時身上的套裝,也跟名牌流行絕緣。
我邁開大步緊跟在她身後。前二十公尺處應該有個地下鐵的入口,只要在那裡跟她展開第一步接觸即可———上級這麼指示我的。
不拖泥帶水,把該做的工作迅速完成,這是我每次執勤的想法;做好分內當為之事,不涉入其他額外情事,是我一貫的作風。
2
等我踏進地鐵樓梯前的屋簷時,已經將傘摺好。摺傘之前,我用力甩了雨傘兩、三次,將雨水甩乾。
附著在雨傘上的泥水,順勢飛到站在我前方的那名女子背上。
我「啊!」地一聲,那片污漬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大。
那女子滿臉疑惑地轉過身來,我立即低頭道歉。「真不好意思,我傘上的泥水濺到妳了!」
她隨即轉過頭,將自己身上的套裝瀟灑地拉開加以檢視一番。等她發現淺棕色的布料上確實沾著一處約五百圓硬幣大小的污泥時,她再次帶著詫異的目光望著我。
她似乎在生氣,不!她當然絕對有生氣的權利,只不過我發現在她臉上還帶著另一種困惑的神情。
就在她打算走下樓梯離去時,我連忙向前擋住她的去路。
「等等!我會替妳出洗衣費。」我提出這個建議。
雖然我還未詳細確認自己的外表,但是聽說我這次不僅是個對年輕美眉充滿吸引力的二十來歲俊俏青年,並且還足以與那些時尚雜誌上的男模匹敵。以上是我從情報部接收到的設定說明。為了調查方便,情報部會事先歸納一些方便辦事的角色,之後再決定我們的外貌跟年齡。
因此,我實在很難把眼前的狀況解釋成,全是因為我的外表使她對我產生厭惡感。果然還是我唐突提到錢,而讓她察覺情況有異吧。
當下她回應了,八成是「沒關係」、「不用了」之類的客套話。只是她說話的音量實在太小,多半只是在嘴裡嘟囔,所以我無法清楚她說話的內容為何。
「等一下!」我下意識差點想伸手抓住她的手腕,但在下一秒鐘及時收手。
因為我忘了戴手套。根據規定,我們禁止徒手觸碰人類身體!一旦徒手觸碰到人類,會使得他們立即陷入昏迷,而導 致整個情況變得異常棘手。因此除了緊急狀況,這種行為是絕對禁止的。違令者必須強制接受一段期間的勞動服務以及講習課程。
縱使我覺得這些小地方的違規,就跟人類隨手亂丟煙蒂、闖紅燈等行為相同,根本毋需一一告誡,可是我還是不曾表達過。因為即使對於某些規定有微詞,該遵守的法規還是得確實遵守。
「弄髒妳身上那件看起來很貴的套裝,我無法置之不理。」
「你說的這件看起來很貴的衣服,上下加起來也不過一萬圓罷了。」從方才到現在,她終於發出能讓人聽清楚她說話的音量。「你這是在諷刺我吧?」
「可是,我真的看不出來那件套裝這麼便宜耶!」老實說,任誰都能一目瞭然。「更何況,如果就這麼放著,髒污會變得更難處理。我想這樣物美價廉的套裝不容易到手吧?」
「不用了啦!只是一點小髒污而已。」她的聲音晦澀。「就算現在再多沾上一、二塊泥巴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說得沒錯!妳的人生並不會因為沾到這塊泥巴就產生任何改變,因為再過一個星期妳就要死了。我心裡這麼想著,但並沒有說出口。
「不行!不然這樣吧,為了表示歉意,讓我請妳吃頓飯如何?」
「啥?」她的表情彷彿是她從未聽過這句話似的。
「我聽說有家不錯的餐廳,可是一個人去總覺得怪怪的,不太敢進去。如果妳肯陪我一起去,那就太棒了!」
她張大眼睛瞪著我。是警戒心吧?人類的疑心病其實很重。他們非常害怕只有自己被當成白痴耍弄;可是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反而更容易被騙。關於這點我覺得他們實在是無藥可救,當然,我也無意拯救他們。
「其他人躲在什麼地方?」她語中帶刺地問。
「咦?」
「他們現在一定正躲在某處笑個不停吧?你們的樂趣就是看我被搭訕時的反應,對吧?」她一口氣說完這一堆話,可是聽在我耳裡卻像在唸經。
「搭訕?」我一臉錯愕。
「我雖然看起來不怎麼聰明伶俐,可是卻從來沒給誰添過麻煩!所以請你們別糾纏著我!」
說完,她隨即轉身離開。沒想到就在那一刻,我一時大意竟然伸手抓住她的肩膀。慘了!當我察覺之際,已經太遲了,只見她轉過臉來看著我。當時她心裡一定想著,我好像看到死神了,事實上,她的確看到了死神。她臉上血色盡失,全身虛脫無力、軟趴趴地坐在當場一動也不動。
這下可糟了!如今懊悔萬分也無濟於事,我只能暗自祈禱這一幕別被其他同事看到才好!
我隨即從口袋裡摸出手套默默地戴上,然後抱著昏厥在地的她站起身來。
3
「你真的……不是在整我?」坐在對面的她對我仍然半信半疑。
她說話的音量之小,實在很難讓人聽得清楚,因此我只得把耳朵湊上前去。此刻我們兩人正相對坐在一家俄羅斯餐廳 的餐桌旁,當我好不容易把昏倒的她弄醒之後,便趁著她意識朦朧之際,半強迫式地把她帶到這家店裡。
「我真的不是在整妳!我只是想表達歉意而已。」
「是……」她抗拒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逐漸泛紅的雙頰。「是這樣嗎?」
「妳剛才突然昏倒,真嚇了我一跳!」老實說,我無法向她說明是因為我徒手觸碰緣故。一旦經我們徒手觸碰的人類,陽壽會縮減一年。不過,這個女人近日內死亡的機率相當高,應該不會構成任何問題才對。
「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昏倒,本來我自認起碼還有身體強壯這項優點。」
我衷心希望她說話時語氣能更乾脆點,這種陰沉的口吻,別說是當事人,就連聽者也會覺得疲憊而心生厭煩。
她小聲地問我:「那……你的名字是?」
我回答:「千葉。」因工作之故而被派遣下凡的我們,每個名字的制定都遵循著一定的規則,那就是不管誰的代稱皆沿用小鎮或都市的名字。縱使每回執行任務的外表、年齡有所改變,只有名字這項條件永遠不變。我想名字之於我們的含意大概就像方便管理的代號一樣。
「妳的名字呢?」
「藤木一惠。」她對我解釋這個名字的漢字意義為一個恩惠。「聽說我的父母希望最起碼我能有一項才能什麼的,因此幫我取了這個名字。很好笑吧?」
「有什麼好笑的?」
「他們恐怕沒料到竟然養出個一無是處的女兒吧。」與其說她在試著搏取別人的同情,倒不如說她只是單純地感嘆自身無奈的際遇,進而自暴自棄來得恰當點。然後,當她把蛋料理送到嘴裡、吞下肚之後,她突然冒出一句話:「我……很難看。」
「很難看?」我當下真的聽錯了。因為我瞇起雙眼看了一會兒之後,再將頭往後移,回答她說:「不會,很容易看。一點也不難看啊!」
聽完我的回答後,她笑了。雖然只是短暫的瞬間,但那笑容卻令她整張臉亮了起來,感覺上彷彿是燈光第一次照映在她臉上。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我的長相並不起眼。」
我「啊」了一聲,卻也無法立刻否定這句話,因為她說得一點兒也沒錯。
接著她問到我的年齡。我回答:「今年二十二歲。」這回的角色設定成跟她同年。
「可是你看起來很老成穩重。」
「大家都這麼說。」這是事實。同事也經常用「穩重」、「冷漠」這類的字眼評論我。實際上那只是因為我不喜歡跟著別人隨便起鬨,再加上我不擅於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但似乎這是種很特殊的性格。
然後,她開始談到工作方面的事,雖然她的聲音依然聽太不清楚,起碼說話的速度變得流利不少。與其說她是因為解除心防而開始暢所欲言,我倒覺得是因為她多喝了幾杯啤酒的緣故。
她說她在一家電機大廠總公司工作。
「那是一流的公司耶,太厲害了!」我盡全力裝出羨慕的樣子。
「可惜只是負責處理客戶的投訴罷了,」她眉頭深鎖的模樣,令她的長相更與可愛絕緣。「我啊,隸屬於客訴處理部,那是個誰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工作。」
「客訴處理?」
「就是接聽來自客戶的電話。一開始客戶的電話會先接到別的服務窗口,但一旦他們覺得客戶態度惡劣,就會立刻將電話轉到我們這個部門,因為我們的職責就是專門處理那些囉哩吧嗦的投訴。」
「聽起來這工作挺苦悶的。」
「對!」只見她此刻垂著肩、滿臉鬱卒地點頭贊同。「真的是鬱悶到不行!打電話來的人全都是牢騷滿腹,不是氣得大聲咒罵,就是竭盡所能說些尖酸刻薄的話,再不就是施以威嚇伎倆。我們每天做的就是跟那些人斡旋,這種日子實在快要把我逼瘋了!」
「好機會!」我心裡暗自竊喜。「每天都飽受煎熬吧?」我不動聲色地引導著她。
「錯!」她搖搖頭,糾正我說:「應該說每天都『極盡』煎熬!」
「這麼難過喔?」我故做同情。
「你別看我現在這副樣子,我接起電話時,還會特地裝開朗的聲音應答呢。雖然說這樣假惺惺對對方很失禮……,然而,當我不斷遭受責罵,總是令我的心情沉到谷底。」
她這時的聲音,宛如冒出泥沼表面卻瞬間破裂的水泡,聽來異常低沉。儘管她剛才提及接聽電話時會特地裝出開朗的聲音,但還是令人難以想像。
「特別是最近有一個怪異的客人。」
「哦?」
「他還特地指定要我聽他投訴。」
「指定?」
「客訴處理部一共有五名女職員,因此轉接過來的電話都是隨機接聽的,偏偏那個人卻指名要我接他的電話。」
「這真的蠻過分的。」所謂跟蹤狂性格的投訴客,就是像這種壞心眼的傢伙。
「是太過分了!」她低下頭,用毫無生氣的眼睛望著我,有氣無力地擠出一抹微笑,說:「真想以死求個解脫呢!」
妳的心願即將實現!我差點脫口而出。
4
「除了工作,有從事其他休閒娛樂嗎?」即使不感興趣,我還是得問一下,這就是工作。
「休閒娛樂?」她的表情彷彿是從未聽過像這般愚蠢的問題。「除了家事以外,什麼也不做。再來就是丟丟硬幣什麼的。」
「丟丟硬幣?」
「我首先會設想:如果是硬幣正面,就表示我會得到幸福。然後就開始拋投十圓硬幣,說穿了,就是簡單的占卜啦!」接著,她露出宛如已經衝破自嘲難關而已然頓悟的表情。「可是啊,每次幾乎都是出現反面。於是,我當下改變規則,決定如果出現反面就表示我會得到幸福,然後再次丟出硬幣……」
「結果竟然出現正面對吧?」
「沒錯!」
「妳不覺得妳想太多了嗎?」
「一想到連百分之五十這種高機率都放棄了我,還真難叫人有勇氣繼續活下去呢!」她大口大口地將啤酒飲盡。「像我這種人,活著像行屍走肉,死了也不會有什麼不同吧。」
「妳如果死了,有很多人會替妳難過的。」我嘗試說些安慰她的場面話。
「是有一個人……」她的身體開始搖晃。「就是那個老是指名要我聽他投訴的歐吉桑……」說完,她露齒高聲大笑說:「我是真的想死,因為從未有好事降臨在我身上嘛。」
老實說,雖然我們從未催促被鎖定的調查對象,但是他們經常把「死」掛在嘴上。箇中原因或許是出自於對死亡的恐懼或憧憬,抑或是心裡早已有面對死亡降臨的萬全準備。總之,每個人都有著相同的表情,彷彿他們正隱身在茂密叢生的雜草堆裡,窺伺著更黑暗的地方,偶爾就拿出來論長道短一番。
據說那是因為人類的潛意識能夠察覺我們死神的真面目。我們研習時也曾論及這點:「死神會帶給人類死亡的預感。」
以實際的例子來說,從遠古時代,就有某些人類可以隱約感應到我們的存在:有些人因「有寒氣襲來」而惶惶難安,也有人「感覺到近日之內死亡即將降臨」進而事先寫下明確死亡預言,還有一些人不但對我們的存在十分敏感,更以占卜之名傳達相關訊息給我們的調查對象。
「想死之類的話,還是別輕易掛在嘴上比較好。」我言不由衷地說。
「日復一日接聽客訴電話,再加上生活裡毫無好事可言,實在找不出任何值得生存下去的理由。老實說,我還真想找人投訴一下我的人生呢。」她說了這句不像她想得出來的台詞。
本來就沒有所謂生存的理由。我忍住沒說出這句話。
「什麼陽壽、命運的,真有這些玩意兒嗎?」她的酒量似乎很差。這下子原本因單眼皮而不起眼的長相,變得更加晦暗了。
根據情報部的資料顯示,她應該鮮少有像這樣跟男性面對面吃飯的經驗,或許是緊張,加上情緒亢奮的因素作祟,她喝酒的速度越來越快。
我們隔壁坐著另一對男女,他們面對面吃飯的樣子,看起來似乎很親密。女子用手摸著肚子,用一種既為難又嬌媚無比的表情說:「人家肚子好撐,再也吃不下了!」坐在對面的男子,立刻用充滿英雄氣慨的聲音回答:「沒關係,我幫妳吃。」只見女子開心極了地道謝,「你好溫柔喔,謝謝!」我著實無法理解,為何把食物跟他人分享的一方會顯得如此開心呢?
「是有陽壽這回事,」我將意識拉回到藤木一惠身上,同時回答她。「只是,無人保證眾人皆能活到陽壽已盡罷了。」
她輕蔑地笑了起來。「這豈不怪哉?人應該皆因陽壽已盡才死吧?不保證能活到陽壽已盡,你不覺得這種說法很怪嗎?」
「如果眾人都因陽壽已盡才死,那可就糟了……」或許不應該告訴她這些事,但見她此刻已經酩酊大醉,於是我接著往下說。
「因為那樣會破壞平衡。」
「破壞什麼平衡?」
「像是人口、環境之類的世界平衡。」雖然我這麼解釋給她聽,其實我也不清楚其中詳情。
「可是人不就該因陽壽已盡才死嗎?」
「坦白說,也有陽壽未盡而死的人,有些人會因突發的意外事故身亡,比方說火災、地震、溺死之類的,這些都不能稱為陽壽已盡、壽終正寢。這些因意外身亡的人跟陽壽已盡的人不同,他們都是事後才決定的對象。」
「由誰決定?」她閉起越顯沉重的眼皮。
原本想誠實回答她「是由死神決定」,但隨即想到這個稱呼帶有輕蔑的意味,因此決定改口回答:「大概是神吧!」其實死神也帶個「神」字,是以我的說辭也不算有錯。
「騙人!」她發出乾澀的笑聲。「如果真有神,為什麼不來幫幫我呢?」她提高了音量,聲音十分澄澈,令我心頭一驚;剛才,我的確瞬間聽到美妙悅耳的聲音。「可是神又是用哪套標準決定誰該生該死?」
「那個連我也搞不懂。」我誠實回答。老實說,關於他們選擇對象時所採用的標準、遵循的方針,我一無所知。說穿了我們分屬於不同部門,我也只是聽從那個部門的指示照章辦事而已。
「可是,如果只因神草率所下的決定而注定得遭逢意外身故,還讓人挺難受的。」
「大概吧。」
「真希望祂們能夠經過仔細調查後再行定奪,要不然可就傷腦筋囉。」她現在說話的樣子就像唱歌一般。說完,隨即 「砰」的一聲,整個人重重地趴在桌上。
「妳說得對!」我心底暗自點頭讚許。那也正是我來此見妳的目的。
經過審慎調查,先評斷是否得對此調查對象執行「死亡」任務,接著將結果向上級呈報。這就是我的工作。
雖說是調查,其實也不是多了不起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在一個星期前與被鎖定的對象進行面對面接觸,期間經過兩、三次的交談,然後向上級呈上「認可」或「送行」的報告,調查作業即告完成。老實說,判斷標準全憑個人自行裁決,因此這套調查制度早已淪為形式,只要沒出什麼大差錯,幾乎所有對象都會以「認可」結果收場。
「啊……好想死喔。」我聽到臉頰緊貼著桌面的她,此刻正喃喃說著夢話。「明天就讓我死了吧。」
我們進行調查的這段期間內,調查對象絕不會死亡。縱使自殺、病死等不屬於死神的管轄範圍,而我們也不知道意外何時會發生。但意外絕不會在我們調查期間內降臨。為此,我懷著些許歉意對她說:「可惜妳現在死不了。」